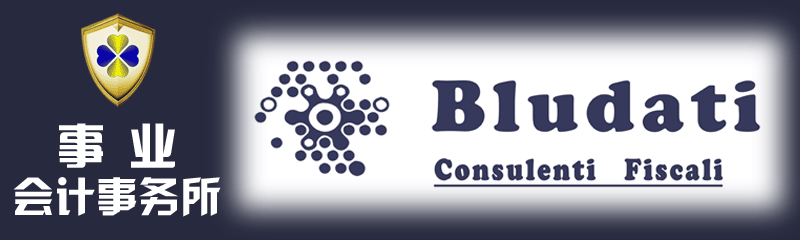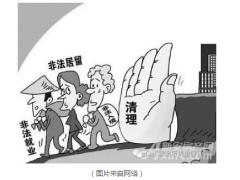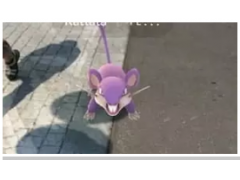享受意大利式慢生活
米兰——最近,我和一对意大利老夫妇聊天,他们的女儿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,又回来在加尔达湖边开了一家餐馆。他们在利古里亚海滨的圣马尔盖里塔有一所朴素的公寓。花园比居住区要大,里面种满了果实像棒球一样大的柠檬树、橙子树和兰花。这对已经退休的夫妇有很多时间可以徜徉在黄昏的馨香空气里。
在我看来,他们的厨房里什么都不缺了:有把帕尔玛火腿切成薄片的机器、空间足以把佛卡夏面包烤得油汪汪的烤箱、一台可以称出200克意面的台秤。他们用橄榄、松子、香肠、兔肝熬成的油润汤汁炖了一只兔子,佐餐的是切得方方正正的煎土豆块,这样切了又煎很是耗时,但每一次耐心的翻搅都是值得的。
兔肉作为美食是被低估了。因为偏见和没有道理的喜爱,兔子在烹饪方面的价值被忽视了。不过意大利人并非如此,他们经常会满怀热情地享用兔肉。
不管怎样,主人谢尔吉奥(Sergio)还是向我回忆起了前去美国探望女儿的经历。拉斯维加斯的贡多拉上高唱的《我的太阳》(O Sole Mio)让人难忘——场景是在“大运河”(Grand Canal)上的里亚托桥下。之后,还有在新墨西哥州的经历,“一连开85英里,完全是直线”。
他看着我说:“一点不拐弯,你能相信吗?”
我能,这让我想起加州的101公路。他却感觉不可思议。意大利的生活总是有一系列曲折蜿蜒之处需要你去适应,丝毫没有自动驾驶的空间。
在这里,人们时常需要灵活适应,而这有时是一种考验。但在另一方面,你还可以享用自家柠檬树产出的柠檬皮,或许还可以再配上三文鱼和200克直通心粉。
那天是5月1日,国际劳动节。这天是假期,可大多数人都在工作,很多商店也都开着。我听到了下面这样的对话:
“今天劳动节啊,怎么所有人都在工作!”
“是啊,不过反正他们在别的日子不工作的。”
“的确。”
像我30年前在这里生活时一样,意大利街头总有人不停地开着玩笑。意大利对现代性挑三拣四,只汲取了有限的部分。意大利的特质里,有那么一部分很抵触将人际互动化约到最低限接触的做法;它有一部分特质十分抵触将每次交流中每一分钱的利润都榨取出来;它还有一部分特质承认,人是需要社区的,也承认陌生人的几句交谈能起到一些作用。在意大利,仍然有纯真的微笑,这恐怕只能称作谦逊,这一点营销学院里是不会教的。它们无法教会你,单调的自我推销会变得多么让人厌烦,最终又多么非人。人们回到意大利当然是为了它的美,但也是为了躲避永不停歇的纷扰。对话在意大利很有弹性的时间观念里自如游走,不再受到作为生产率衡量标准的时间的束缚。
在药店里,最好要有处方,但规矩总可以灵活处理。我听到了这样的对话:
“我们不住在意大利。”
“那就更好啦!”
“为什么呢?”
“在这里做所有事都很难。”
的确。比如意大利就没有搞定“效率”这个东西。我在几十年之后第一次来到米兰的利纳特(Linate)机场,我发现下飞机到航站楼要坐同样笨重的巴士。ATM机是坏的、问询台没有人。奇怪,米兰的2015年世界博览会(Expo 2015)刚刚开幕,现在不收拾收拾,还等什么时候呢?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保障食品安全、打击浪费(在这个方面意大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)、改善营养(还有什么能比那只兔子更棒)、保护环境。
在5月1日开幕当天,一群自称是“黑暗势力”(Black bloc)、穿着帽衫的反资本主义混混,在米兰市中心漫无目的地打砸,对作为资本主义事业的世博会表达抗议。他们殴打警察、纵火焚烧汽车。在之后的周末,米兰民众走上街头,带着海绵、抹布、清洁剂和肥皂,下定决心要清洁整个城市。他们很快就做到了。
在意大利,国家力量依然很弱。但是社区——家庭、朋友、市镇、地区——往往都很强大。在评估意大利的状况时,往往会低估这些在面临困难时充当缓冲的纽带有多么有效。
年轻的意大利总理马泰奥·伦齐(Matteo Renzi)刚刚推行了一项重大的选举改革法案,旨在终结近乎顽固的政府不稳定的问题。这项法案大体上保证,只要获胜的政党赢得40%的选票,该党就能得到奖励,保证它能在有630个席位的议会里得到340个席位。(如果没有一个政党能得到40%的选票,则两大政党进入第二轮投票。)
或许这个举措能像伦齐希望的那样,产出更多的直线——政府能坐满五年的任期,这对意大利是有益的。但还有很多其他的弯要拐。